
当古二发布第三波录音时,所有人都聚焦于王家卫的回应,却迟迟未见编剧圈内的任何公开声援。这场看似“同归于尽”的对峙,将中国编剧的生存困境暴露得淋漓尽致——没有署名、没有话语权、稿酬微薄,想要维权又害怕被行业封杀,沉默与忍让成了普遍的生存策略。

然而,就在这件事的热度尚未散去时,又有两位编剧的维权经历浮出水面,尽管没有录音的爆料冲击力,但却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行业的普遍困境。
古二录音中的一段内容,提到一名月薪三千的编剧,在完成了编剧和助理两重角色后,仍然无法获得署名的情况,这种全程参与创作却始终被剥夺认同的困境,让不少同行感同身受。然而,直到今天,除了《繁花》剧组曾发布过“回到国内合理合法维权”的声明,几乎没有任何知名编剧敢于公开表态。
这些沉默并非因为不想伸出援手,而是因为不敢帮忙。行业论坛中有匿名编剧透露,自己也曾面临过类似纠纷,可一旦公开表态,自己下次接项目时可能就无人敢用。毕竟,在这个圈子里,“听话”有时比“写得好”更能确保拿到工作机会。

2025年9月末,编剧李某在影视行业协会的公开投诉平台上提交了完整材料,诉说了自己在去年参与某校园网剧的编剧经历。为了迎合一位流量演员的要求,导演擅自删改了三分之一的剧情,甚至将李某的高光台词分给了其他角色。最终,播出时,剧组的署名栏里只有“总编剧”与两位改编编剧的名字,李某的贡献根本未被提及。虽然他与制作方沟通,要求公正署名,但对方仅提出2万元的“劳务补贴”,还要求他签署保密协议,不得泄露纠纷详情。为了避免影响后续工作,李某无奈签字,只能匿名上传聊天记录、剧本修改痕迹和合同截图。虽然行业协会随后对该制作方作出了违规通报,并要求其限期整改,但李某的署名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
展开全文实际上,在韩国和美国,编剧的遭遇与中国的截然不同。今年10月初,韩国一线编剧金恩淑与SBS电视台签约了120集的新剧《时光回信》,合同中明确规定编剧拥有角色选择权和剧本修改的最终决定权,签约当天她便收到了60%的稿酬,剩余部分将在每播出20集后按时结算。
美国的情况也不遑多让。2025年9月,美国编剧工会更新的《基础协议》新增了一条关于“AI生成内容不得替代人类编剧核心创作”的条款,此外还要求流媒体平台公开剧集播放数据,确保编剧分成透明可查。得益于去年美国编剧大罢工,编剧的平均稿酬上涨了15%,署名纠纷的处理周期也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
回到中国,编剧的困境与国内影视行业的模式密切相关。中国的电视剧通常需要先经过审查才能拍摄播出,这使得“边写边播”几乎不可能。而在拍完剧集后,编剧交完剧本便几乎失去了话语权。导演为了拍摄方便可能会改剧情,演员为了自己的形象也可能加戏,制作方则可能为了流量调整故事情节。

例如,去年某部古装剧中,编剧原本设定的女二号是贯穿全剧的核心反派角色,但由于演员团队以“影响艺人形象”为由要求改动,女二号最终变成了正面角色,剧情的逻辑也因此被彻底打乱。编剧提出反对时,却被告知“演员流量大,能带动收视率,得听演员的”。

当编剧的权力如此微弱时,稿酬自然也无法提高。2025年10月,影视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80%的青年编剧单集稿酬不足1万元,而头部演员的单集片酬却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更为无奈的是,稿酬拖欠现象普遍存在。编剧王某在2025年8月接了一部网络电影剧本的工作,合同中写明“完成初稿支付50%,定稿后一周内支付尾款”。王某按时提交了定稿,但制作方却以“剧本不符合市场需求”为由拒绝支付尾款,甚至将他的剧本稍作修改后拿去拍摄。王某咨询律师后得知,走法律途径维权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且律师费昂贵,最后只能选择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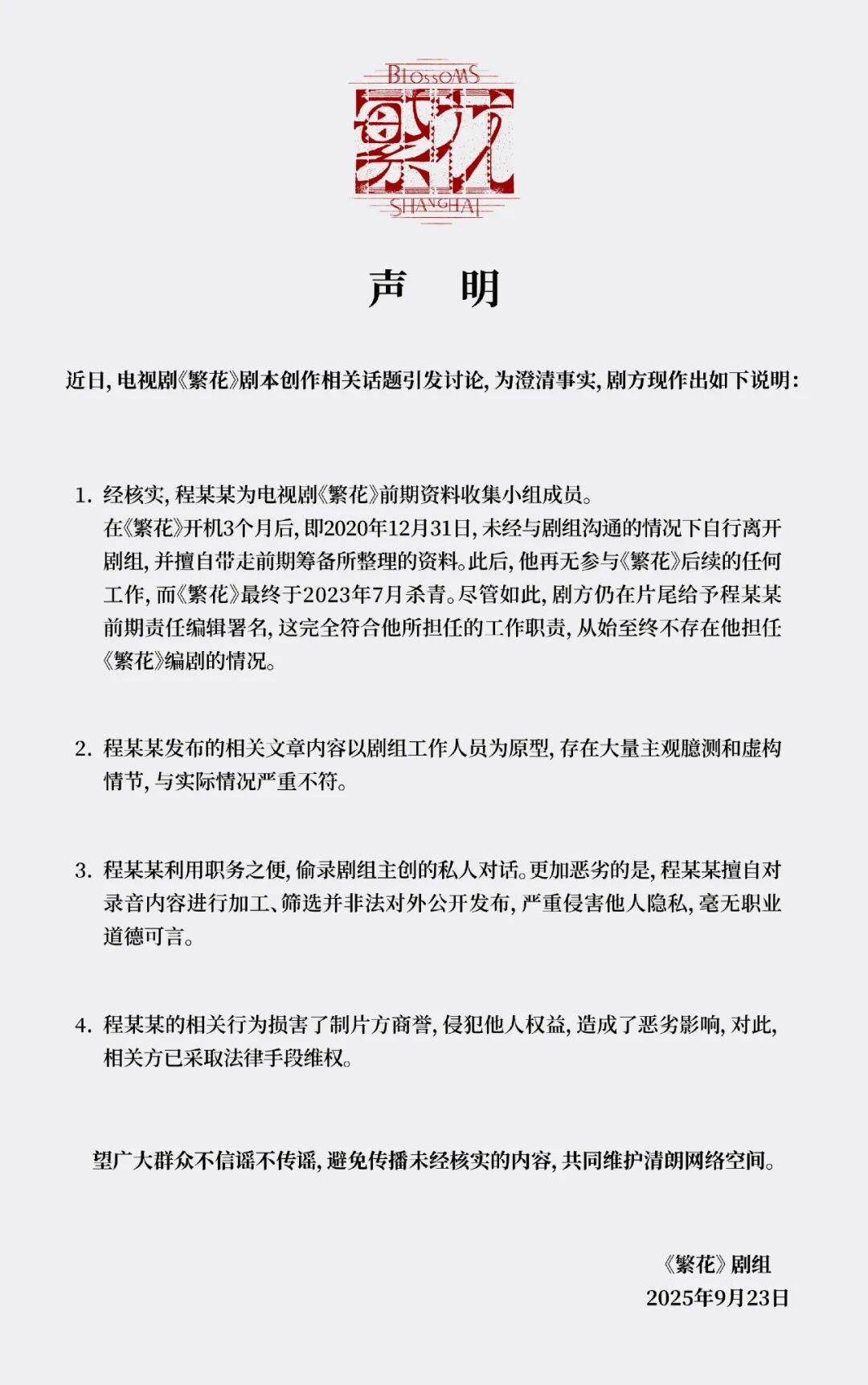
中国编剧的生存环境要改善,的确需要时间。但随着行业协会投诉平台的逐步完善,以及越来越多编剧愿意站出来分享真实经历,规范创作环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只要相关规则不断完善,编剧们终究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赢得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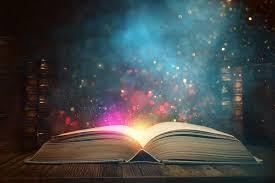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