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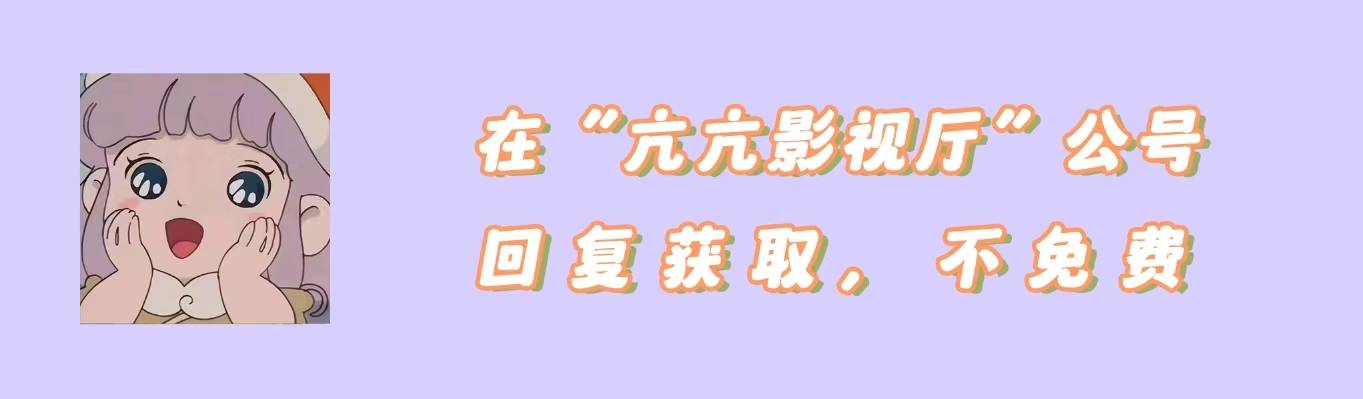
2025 年韩国影坛,朴赞郁筹备 17 年的《无可奈何》以横扫青龙奖六项大奖的姿态,成为现象级作品。这部改编自唐纳德・维斯雷克小说《斧头》的黑色喜剧,延续了朴赞郁一贯的诡谲风格,却跳出了 “复仇三部曲” 的个人恩怨叙事,将镜头对准了经济下行时代的中产生存困境。影片用一个 “为求职而清除对手” 的荒诞故事,以冷峻的幽默剖开了新自由主义下 “无限竞争社会” 的残酷真相,既让观众在荒诞情节中会心一笑,又在笑声过后陷入对人性异化与社会焦虑的沉重思考,堪称继《寄生虫》之后又一部直击阶层痛点的韩国电影力作。

影片的叙事魅力在于将极端行为包裹在日常化的绝望之中,让荒诞显得合情合理。主人公柳万洙(李秉宪饰)是造纸行业 25 年的资深技工,拥有令人羡慕的中产生活,却在公司被美方并购后的大规模裁员中一夜失业。长达一年的求职之路,耗尽了他的积蓄与尊严:简历石沉大海、面试中被年轻面试官质疑 “技术过时”、房贷即将断供、孩子学费无以为继。这些极具现实质感的困境,精准戳中了全球中产的集体焦虑 —— 他们看似拥有稳定的体面,实则如同风中残烛,一场失业就足以摧毁所有。当柳万洙在又一次面试失败后,看到竞争对手的简历时,那个疯狂的念头应运而生:“除掉他们,我就能得到工作”。朴赞郁没有将这一转变处理得突兀惊悚,反而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生存压力下的理性崩塌,让观众在恐惧之余,竟生出一丝 “无可奈何” 的共情。

黑色幽默的极致运用,是影片最鲜明的风格标签。朴赞郁曾明确表示,希望观众能从这个苦涩的故事中读出笑声,而李秉宪也精准捕捉到了这种 “含泪的幽默”。柳万洙的第一次 “清除行动” 充满荒诞感:他笨拙地模仿电影里的犯罪手法,却在过程中频频出错,甚至因过度紧张而打翻东西,让一场血腥的犯罪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这种反差感在影片中无处不在:他穿着得体的西装去 “执行任务”,仿佛只是去参加一场面试;在处理 “痕迹” 时,还不忘整理好自己的领带;面对妻子(孙艺珍饰)的疑惑,用 “工作太忙” 的借口敷衍,却在转身时露出慌乱的眼神。这些细节既消解了暴力场景的不适感,又强化了悲剧的内核 —— 当一个恪守规则的中年人,被迫用犯罪的方式维持 “体面”,本身就是对社会规则的最大讽刺。正如 BBC 评论所言,影片将 “劳动者之间的残酷竞争” 以荒诞喜剧的形式呈现,让绝望变得既可笑又心酸。

朴赞郁在影片中展现了成熟的作者风格与创新突破。作为以悬疑惊悚闻名的导演,他此次将个人风格与社会议题完美融合:标志性的诡谲镜头语言、充满隐喻的场面调度,都为故事增添了深层张力。影片的色彩运用极具象征意义:柳万洙的家始终笼罩在温暖的暖色调中,象征着他想要守护的家庭温情;而求职场景、犯罪现场则多用冷色调,凸显外部世界的冷漠与残酷。这种色彩对比,暗合了主人公内心的撕裂 —— 他渴望维系家庭的温暖,却不得不游走在黑暗的边缘。同时,朴赞郁没有延续《分手的决心》中的浪漫悬疑,而是转向了更尖锐的社会批判,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影片中,公司并购、人工智能替代人工、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等元素,都是对当下全球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让这部作品超越了地域限制,引发广泛的国际共鸣。

李秉宪的表演堪称影片的灵魂所在,他用教科书级别的演绎,塑造了一个复杂立体的 “悲情罪犯”。柳万洙的眼神变化贯穿始终:失业初期的迷茫无助、求职时的卑微讨好、决定犯罪后的决绝挣扎、得手后的惶恐不安。在一场家庭聚餐的戏中,他看着妻子和孩子的笑容,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眼底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恐惧,将内心的煎熬展现得淋漓尽致。李秉宪没有将柳万洙塑造成一个天生的恶人,而是突出了他的懦弱与无奈 —— 他不是主动选择作恶,而是被社会压力逼入绝境。这种 “非典型反派” 的塑造,让角色更具现实意义,也让影片的批判指向更为明确:真正的 “凶手”,是那个将人逼至绝境的 “无限竞争社会”。孙艺珍、朴熹洵等配角的表演也相得益彰,尤其是孙艺珍饰演的妻子,看似温柔贤淑,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生活压力的感知,为故事增添了细腻的情感层次。
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对社会议题的尖锐剖析。正如韩国作家金敬哲在《坐困穷途》中所描述的,韩国社会早已陷入 “过度资本主义” 下的无限竞争,“为了成功不择手段” 的风气蔓延,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柳万洙的遭遇,正是这种社会机制的牺牲品 —— 新自由主义将 “经济竞争” 奉为唯一法则,将个体价值简化为经济价值,让劳动者在 “不进则退” 的焦虑中疲于奔命。影片中,没有绝对的恶人:解雇柳万洙的公司只是遵循 “资本逻辑”,年轻的竞争对手只是正常求职,柳万洙的妻子也只是渴望安稳的生活。所有人都在规则内行事,却共同酿成了这场悲剧。这种无差别的批判,让影片的社会寓言更具力度。朴赞郁在采访中也提到,影片探讨的就业危机、中产焦虑等问题,是全球同步的时代议题,这也是作品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核心原因。
结局的处理堪称点睛之笔,柳万洙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却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平静。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坐在办公室里,眼神空洞,耳边不断回响着那些 “竞争对手” 的声音。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给出救赎的答案,反而强化了 “无可奈何” 的主题:在无限竞争的社会中,个体的挣扎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生存,却永远无法摆脱被异化的命运。正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 —— 那把用于 “清除对手” 的斧头,最终变成了悬在自己头顶的利剑。
《无可奈何》之所以能成为年度佳作,不仅在于其精湛的艺术表达,更在于它的现实意义。它用一个荒诞的故事,撕开了中产体面的伪装,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下个体的生存困境。当影片落幕,柳万洙空洞的眼神仿佛在追问每个观众:在残酷的竞争法则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这部作品既是对一个时代的深刻批判,也是对每个挣扎者的温柔共情,它提醒我们:当生存成为唯一的目标,人性的光辉便会在不知不觉中熄灭,而这,正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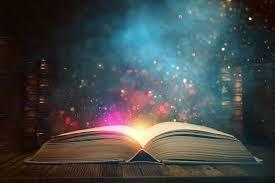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