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一迁
近年来,沉浸式艺术展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尤其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夏天,此类展览格外引人注目:浙江省博物馆《相无古今——石窟艺术超感沉浸体验》通过“实物+数字沉浸”方式呈现七大石窟艺术精华,观众可穿戴VR设备,在AI数字人引导下开启一场奇妙的感官之旅。在上海,中华艺术宫推出的《山海经之烛龙秘境》沉浸式裸眼3D装置艺术展,利用全息激光、互动传感等前沿数字技术,开启可感可触的时空对话。
沉浸式艺术展邀请观众进入由技术编织的一个具象化的场景,创造出全新的可感、可知、可触的审美体验。
今天我们谈起艺术,“场景”一词愈发凸显,艺术展被看作是构建体验、生成关系、唤醒情感的场所,无论是快闪艺术,还是城市公共装置,都超越了传统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被感知、被体验、被参与的场景。沉浸式艺术展正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当你看展时,展览也在回应你
在传统中国的美学思想当中,“沉浸”即游心、无我。老子主张清除杂念,以合于道,庄子以“心斋”和“坐忘”来阐释主体的超越与物我的合一,后世文人也多强调在审美想象当中实现自我与世界的感通。
传统语境中的沉浸,是一种观众由内而外生成的主体意识,通过感情投入达到感官的延展,从而完全进入艺术作品的世界中,得到意识上的审美享受。
1967年,作为互动影像之开端,捷克影片《一个男人和他的房子》打破艺术与媒介、受众的关系,亦打破了静观方式。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沉浸式艺术通过新的展现手法、数字信息的技术化处理、声光电参与的环境营造使大众与环境高度融合,在观影、观展中与空间、艺术作品交互,制造沉浸体验。从日本艺术团队teamlab开始,展览流行起将光影装置充斥在整个空间作为作品的方式,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观众仿佛逃离了现实世界,得到目不暇接的视觉震撼。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雨屋》则通过3D镜头监测观众的实时运动情况,使观众行走在被大雨笼罩的空间中也不会淋湿。这个仿佛魔法一般的艺术作品,让观众得到了奇妙的体验,也和空间进行了跨感官对话。
数字时代的“沉浸”,几乎等同于重新为观众构建可见的、具体的场景。从湖南博物院的《生命艺术:马王堆数字艺术展》到遇见博物馆的系列展,当下的展览纷纷依托数字技术,将沉浸具象于可被操纵、可被建构的场景中。从中我们看到,沉浸式艺术通过数字信息的技术化处理,声、光、电参与的环境营造,使观众高度融入这个空间,在虚实结合中,个体获得临场的幻觉、心理的共鸣等具身性经验,实现和艺术作品的交互,它突破了传统艺术对象性、稳定性审美经验的局限。
场景的创新也促使置身于艺术作品或者展览之中的观众,经历了一系列审美变化:
通过算法,数字技术构建出一个与现实并行的世界,它是脱离现实的,但同时又重构了一种真实。就像各种VR展,人们在虚拟的空间里获得的却是真实空间的感受。
在数字化的沉浸式艺术面前,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审美能力这些限制都被解除了。比如上海博物馆引进法国Excurio团队打造的沉浸VR展《消失的法老》,在数字技术构建的超真实的语境当中,赋予受众夜间参观胡夫金字塔的“超级VIP”身份,观众由观看者转为参与者,由外部的凝视走向身体的在场,其行为、情绪、节奏成为艺术生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延展的感知,激活了人对艺术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参与者的感情共演让艺术成为生命化的过程。
科技赋能以后,艺术作品对于观众而言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看沉浸式艺术的观众特别多,通过空中行走、触发装置或者身体互动,观众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他在互动中持续输出感官感受和情绪价值,让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地方安放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在沉浸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满足。所以观众对于艺术作品沉浸式再现天然是有所期待的,这种审美期待的升级也刺激艺术和艺术展览不断迭代更新,回应观众。
此外,部分沉浸式艺术展超越了传统的展厅,进入商场、进入地铁,打破了传统艺术空间的界限,形成了一种实践性和情境性高度融合的美学图景。例如海南一家免税店,将整个商场打造成数字艺术的展示空间,配合不同材质的载体,呈现出美轮美奂的效果。
酷炫背后的隐忧
但这种技术与场景的融合也暴露出一些隐忧。比如,审美的主动性被消解了。如果我们习惯在欣赏艺术的时候被预设引导,被投喂既定的审美经验,就容易丧失对艺术深层次意图的思考。就像美国媒介文化学者波兹曼说的,人们因为享乐而失去了自由。
观众对沉浸冠以更高的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景观、影像被创造出来,观众对于美的感知也会逐渐钝化,如果一切皆美,那么又何处是美呢?
被动的沉浸替代了艺术的原真价值,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并且一些沉浸式艺术展完全脱离了原作,以数据、技术、符码取而代之,阻隔观众和原真作品的同频共振。
最后,是廉价的审美体验。在传统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会静下心来,全神贯注投入对象,去细细品味经典之作,构成一场富有深度和哲思的艺术交流。但在数字化沉浸式艺术中,艺术已经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只注重视听效果的呈现,而非艺术的本质。这种审美体验是泛化的、浅表化的,走向了带有娱乐性质的艺术狂欢。
超越感官
经过数字化演绎的传统艺术作品,在脱离了数字化后,也不见得有普通观众还能认识,将作品名与作品对应起来。这究竟是传播了这件艺术作品还是异化了这件艺术作品?不断泛化的沉浸场景也揭示出新时代艺术审美和媒介之间复杂的张力。
沉浸世界的构建关键在于观众的参与和介入,从艺术对象的旁观者转变为艺术情境的亲历者,并且产生忘我的体验和心理的满足。数字时代沉浸式艺术展的创新之处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此类展览的野蛮生长也让我们有必要警惕随之而来的一种审美困境,寻找多重的沉浸可能。
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载:“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对于当时的僧侣们来说,幽暗的洞窟是他们修行、神游的场域,借山水壁画与天地交流、冥思,架空凿岩的佛龛似抚慰人心之所在。这种凝神状态何尝不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前不久,在上海一个小众美术馆里,有个名叫《色·见》的展览。其中有一件作品是艺术家将身边唾手可得的红色物件,诸如老旧的证件、勋章、奖状、笔记本等拼接起来,形成一条高低错落的线。作品承载了时代的变迁,观众饶有兴致地翻看,有新奇,有感叹,有怀旧,有唏嘘,完全进入作品中,因年龄和经历的不同,产生各种不同的体验。没有数字科技的加持,同样也以亲身探索引发纯粹的精神漫游和内心观照,这个展览向我们宣告了沉浸式艺术展的其他可能。
不可否认,数字化的沉浸式艺术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了艺术价值深刻的转型,还有审美体验全面的革新。不过唯有当场景和思想相连,当体验与感悟重构,沉浸式艺术才能真正的成为超越感官层面表象的东西,回归到艺术的本质。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美术设计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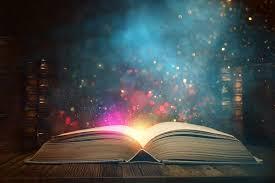)
)
)
)
)
)
(红霉素软膏能促进肛裂愈合吗))
)
有限公司:无货源模式的供应链弹性,如何通过“轻连接”实现“重协同”?(鼎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