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林志忠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电子物理系)
本文选自《物理》2025年第11期
经典超导体理论称为 Bardeen—Cooper—Schrieffer (BCS)理论,其中第二位作者库珀 (Leon Cooper, 1930—2024)在构思及建立该套理论的参与过程与杰出贡献,可谓是潇洒走一回,“事了拂衣去”(李白《侠客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2017年1月中旬,在布朗大学物理系为 J. Michael Kosterlitz 荣获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举办的全系师生欢庆会上,库珀(左)和Kosterlitz的合影(取自欢庆会影片)
1950年代初期,超导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巴丁(John Bardeen,1908—1991)无疑是其中一员大将,他置身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一望无际玉米田中,带领着几位初出茅庐的博士后和博士生,挺身攻坚。最初的两位博士后包括李政道(1926—2024)和派恩斯(David Pines,1924—2018)(后来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助教Francis Low也加入了他们的研究行列),但到了1955年夏天,两人都已离开了伊利诺伊大学。
派恩斯与巴丁共事三年(1952—1955),两人深入探讨了金属中的电子和声子(量子化的晶格原子振动)作用问题,这是迈向超导体理论的重要一步。派恩斯于195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职位,前往任教,因此巴丁着急寻找一位既“精通场论并愿意从事超导性研究”的同事,与他一起破解超导体之谜。经巴丁向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询问,杨振宁(1922—2025)向他推荐了库珀。库珀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核子理论,精于量子场论和多体作用问题,但他对固体物理一无所知,甚至未曾听过“超导体”一词。
1955年9月,几经思考之后,库珀欣然接受邀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他一边在巴丁指导下自学超导体物理,一边向物理系同仁讲解量子场论及其计算方法。埋首学习与探究仅约一年时间之后,他已构思出超导 “电子对”(Cooper pairs) 的概念并完成计算,且将论文投稿到Physical Review (1956年9月),于11月中旬刊出。
紧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BCS三人比往昔更加勤勉工作,奋力抢关计算,因为巴丁非常担忧天才横溢的费曼会捷足先登,率先提出一套理论解答超导性问题。1957年7月,三人终于完成复杂庞大的计算,并把长达30页,标题直截了当更直指核心取为“超导理论”(Theory of Superconductivity)的论文投至Physical Review,于12月刊登。时年,库珀27岁,施里弗26岁,巴丁49岁。
这篇青史留名的BCS超导理论论文投稿之后,库珀也就离开了伊利诺伊大学,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58年,他转任布朗大学的副教授职位,不久晋升为讲座教授,直到2024年10月逝世,享年94岁。
所以,库珀只在伊利诺伊大学待了两年,这也几乎是他学术生涯中仅有的专注于固体物理学课题研究的两年。库珀的最爱是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1973年他在布朗大学创立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研究所”(Institute for Brain and Neural Systems),对该领域贡献良多,而且他是一位人工智能的先驱。——据说,库珀从中学起就最喜欢生物学,但他觉得读物理要趁年轻,而且他认为研究物理能让人对复杂的自然现象培养深刻的洞察力,因此高中毕业后他选择就读物理系和物理研究所。
1972年,BCS三人因(后来)以其姓氏命名的超导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时刻,派恩斯心中不知是否曾隐约浮起一丝幽微苦涩之感,因为利用场论方法计算电子—电子以及电子—声子的多体作用性质,也是他的专长。然而,世间有几位年轻人(及资深学者)能抗拒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教职橄榄枝?况且,在他离开伊利诺伊大学的1955年夏天,巴丁(以及全球的物理学家们都)还缺乏明确无疑的头绪,尚未找到撬开超导理论大门的具体可行敲门砖,而学术资历稚嫩的施里弗(John Robert Schrieffer,1931—2019)才刚刚选择了超导理论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库珀则仍完全是个固体物理学的局外人。
库珀后来曾经半开玩笑地回忆说,如果他不是个局外人,知道超导体自被发现之后的40多年间(从1911年至1950年代中期),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泡利、费曼和朗道,以及其他无数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都曾绞尽脑汁,费力尝试解开超导机制之谜,但最终全部功败垂成,很可能他当初就一口回绝了巴丁的邀请,逃之夭夭了。又,巴丁深思熟虑,洞烛机先,深知要攻克超导理论难关,必须邀请一位像库珀这样精通量子场论的年轻人参与,显然他能获得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绝非侥幸!
后 记:落笔写完这篇短文之后,并回想先前《安德森局域化理论的起源》一文(《物理》,2023,52(5):361),突然意识到库珀和安德森两人的漫长学术生涯与人生,似乎“没有交集”。安德森年长库珀7岁,生于1923年,卒于2026年,两人都是美国人,都长年居住于美东海岸,且都长寿,又都是凝聚态物理学泰斗,(从科学文献上看来)却几乎没有互动,不免令人好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库珀从1970(甚至1960)年代起就转换跑道、离开凝聚态物理学研究,但这一点理由似乎不够坚实充分,因为安德森与许多不同领域和方向的杰出学者都有往来。况且,库珀的最爱是“复杂(生物)系统”,而复杂系统正是安德森据以提出后来让他扬名立万的“More is different” (多则生异)观点的重要基石。另外一个理由,则有可能是源自“瑜亮情结”吗?当26、27岁初出茅庐的库珀埋首破解超导性这一著名世纪谜团——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圣杯”——之时,安德森正心无旁骛地专心于建构他的无序系统中的局域化理论,及构思(非磁性)金属中的(杂质)局域磁矩如何形成,这不但使得两人的学术兴趣与焦点错身而过,更让安德森比库珀晚了5年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会因为错过成为超导理论之父(安德森也热爱并关注超导体物理)而耿耿于怀吗?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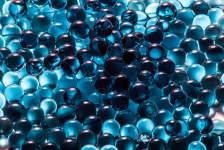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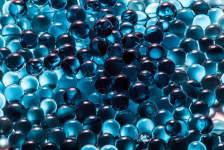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