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哇塞,小伙伴们,现实主义电影界最近可是发生了大事情哦!那些曾经宏大叙事的疲惫感,让创作者们纷纷回到生活的细微处去寻找意义。这不,我们的《震耳欲聋》主创团队就是以创作本能建立了一种平衡的类型语法,既有叙事强度,也有生活密度,简直太酷了!
影片由新人导演万力执导,故事取材自真实事件——CODA(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健听者)律师张琪的经历。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别急,这部影片可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重新定义了“发声”这件事。
影片没有把聋人描绘成单纯的受害者,而是把他们放进一个有欲望、有分歧、有误解的真实世界;也没有让律师成为英雄般的救世主,而是让他在一次次失败和迟疑中,慢慢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听见”。
万力和编剧汤禹辰的这部首部大银幕作品,不求惊人,而求准。在这个国庆档,他们以自己的姿态,贡献了极高的完成度。这部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讲述了一个关于维权的故事,更在于提醒我们,当一类题材的表达变成了趋势,真诚的突破该从何处着手。
影片的叙事结构沿袭了现实主义的经典叙事模型,但将叙事视角再分配,将听障群体重新带回复杂的社会生态。主角李淇的背景设定极具类型张力,他既是“能沟通的人”,又是“被拒绝沟通”的人。他的成长过程,被聋人这一群体带来的,更多是难言的自卑和彷徨。
影片的视听设计也非常出色,导演万力通过降噪、滤波、突发静音与环境声放大,重塑观众的听觉经验。尤其是开场十五分钟左右的回大院段落,营造出一种降噪后的真实,让观众通感其中,进一步融入聋人世界的时间感。
演员的表演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檀健次的李淇是近年少见的灰度男主,他的表演虽内敛,但又有着清晰的情绪线。兰西雅的张小蕊则延续了她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力量感,角色的硬度和脆弱被均衡得恰到好处。
总之,《震耳欲聋》用类型化的视听和人设把根扎实,减少了用苦难博同情的表达逻辑,转而建立起一种更平视的观看姿态,让聋人群体自己成为叙事的主体。这部影片的好口碑,证明了真诚仍然是最稀缺也最有效的生产力。
当下,现实主义正在经历一次微妙的转向。宏大叙事的疲惫,逼迫创作者回到细微处去寻找意义。而《震耳欲聋》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现实题材仍有被克制讲述的可能。这种克制靠建立平等的共处姿态,也是一种更深层的伦理姿态。
THE END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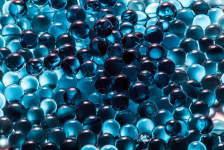)
)
激光市场调研报告-主要企业、市场规模、份额及发展趋势(深紫外激光 应用))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