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台湾抗日志士后代郑岚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受邀参加纪念展览、出席座谈会,并讲述祖辈的抗战往事。尽管满头银发,但他的目光坚毅,谈吐铿锵。

“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就会讲下去。”郑岚轻抚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声音低缓却坚定地说起父亲郑坚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这个抗战老兵还等着听到祖国统一的一声春雷。”
这一声“春雷”承载着三代台胞的家国记忆与民族情怀。从爷爷郑约在抗战时期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到父亲郑坚加入台湾义勇队亲历台湾光复,再到如今郑岚用自身的讲述传递记忆与信仰,这个家庭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深刻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约与挚友谢真、张水民决定以死相搏,潜入厦门鼓浪屿向日本领事馆投掷炸弹抗议日本侵华。炸弹藏在年糕下面,由谢真夫人提篮带入,躲过军警检查登上了船。所投炸弹虽然威力不大,但引起现场一片混乱,起到强烈震慑作用。郑约早年参加了“台湾文化协会”,反抗日本殖民统治。1930年因街头演讲被通缉逃亡到大陆,改名郑约,号抱一,意指“抱定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家必将统一的信念”。
1942年,郑约加入台湾义勇队,投身抗战十几年内,他是街头高喊抗日救国的带头人,是夜潜敌区的情报员,还是台湾义勇队闽南通讯处主任(中校军衔)。他曾两次偷渡厦门,藏在下水道、涵洞中长达数日,只为掌握日伪军情。他深知自己九死一生,因此留下绝笔信,告诉家人如何脱身。“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特意在信封上注明‘三天后才能拆开’,然后悄然离家。家人看过信件后,个个泪流不止。”郑岚回忆道。
台湾义勇队队员臂章上仅有“复疆”两个字,即为光复中国固有领土台湾而战斗。这是千千万万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抗战时期,超过5万名台湾同胞来到大陆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不少人为国捐躯,用生命诠释了身为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
1945年,在郑约的影响下,郑岚的父亲郑坚刚满18岁时也加入了台湾义勇队。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郑坚随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上校先遣返台,成为第一批从福建奉命返台的义勇队队员。他们在台北街头升起了第一面国旗,那一刻,台湾街头巷尾掌声雷动,许多台胞热泪盈眶,久被压抑的家国情怀喷薄而出。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同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中间有70天的权力真空期,台湾义勇队在这段过渡期承担了重要职责:看管日本遗留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安抚民心。队员们都是台湾人,既熟悉故土又参加过抗战,回到台湾后受到民众高度信任。
1947年,郑坚被保送进厦门大学。带着台湾光复的喜悦和读书报国的热情,他再次踏上大陆。没想到此行与家乡一别就是30多年。1949年寒假期间,地下党组织鼓励共产党员上山下乡参加武装斗争,他再次投笔从戎,毅然脱下学生装换上农民服,从厦门潜入安溪、永春一带山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从加入义勇队到参加解放军,再到1974年调任“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郑坚一生三次穿上军装。去年,98岁的郑坚弥留之际,留下最后一句话:“我这个抗战老兵还等着听到祖国统一的一声春雷!”
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台联刚刚创办,郑岚在父亲郑坚的影响下入职省台联,走上了从事对台工作的道路。那个年代的两岸交流,很多时候要靠心意。1982年,福建省台联发起一项名为“鸽子·鸽子回家吧”的活动,通过福州市信鸽协会寻找飞失的台湾信鸽,在它们脚上套上写有“福建省台联向台湾同胞问好”的脚环,然后由平潭渔民在海边或出海时放飞,让信鸽把乡情和祝福带到海峡彼岸。
退休后,郑岚担任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继续挖掘和讲述那段硝烟中的红色历史。他说,福建老区人民在抗战时期曾向主战场输送2400多名新四军战士,“这是两岸同胞并肩抗日的又一印证”。
80年足以让记忆模糊,却无法让血脉断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消息一出,郑岚感慨万千:“这是台湾属于中国在法理层面的重要一环,也让我们这些台湾抗日志士后代心中更加踏实。”
那天,郑岚轻轻捧起家中那张全家福照片,眼神温柔却坚定。“爷爷和父亲的一生,是台胞同仇敌忾抗日、渴望两岸统一的一个缩影。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完全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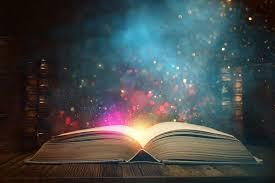)
)
(为什么有人喷香水一路上都香))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