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揭露了一起涉及金额超过2000万元的循环骗贷案件。刘某通过“租牛-抵押-再租牛”的方式,从公主岭华兴村镇银行和吉林银行骗走贷款超1480万元。刘某使用顶名贷款、虚假合同等手段进行连环诈骗,银行内部人员涉嫌收受“好处费”为审批开绿灯。这起骗局背后折射出地方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的系统性失守。
作为吉林省内唯一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吉林银行自2024年以来已收到31张罚单,累计罚款450万元。频繁的监管处罚暴露出该行在贷前调查、贷后管理、风险分类等关键环节存在严重缺陷。从业绩数据看,上半年实现营收88.44亿元,同比增长9.48%,全年预计约180亿元。但在规模扩张的背后,内控失守、风险累积的隐患正在发酵。
2022年6月,刘某从别处租来297头活牛,找到任某充当名义借款人,以这些“借来的牛”作为抵押物向公主岭华兴村镇银行申请贷款。由于银行未核实牛的产权归属,400万元贷款顺利发放。两个月后的8月,刘某故技重施,用新租来的牛再次申请贷款,又成功骗取500万元。随后,刘某将目标转向吉林银行。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刘某先后以徐某及其子的名义,使用虚假购牛合同和活体牛抵押方式,分两次从吉林银行骗走300万元和280万元。贷款发放后,刘某擅自改变贷款用途,将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并私自出售抵押物。
这起骗局能够得逞,暴露了银行在贷款审批流程中的多重问题。首先是抵押物核验流于形式。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未核实牛的产权归属,对于活体牛这类特殊抵押物,既没有查验购买凭证,也未核实养殖场的实际经营情况,完全依赖借款人提供的虚假购牛合同。其次是贷前调查严重失实。吉林银行松原乾安支行因“贷前调查失实”被罚款30万元,三任行长因此被警告。正常的农业贷款审批应当包括对借款人经营能力、资金用途、还款来源的详细调查,但从案件细节看,银行显然未能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刘某能够在短时间内以不同名义在同一银行系统内多次骗贷,说明银行的客户信息系统和反欺诈系统形同虚设。
此外,吉林银行直到2023年4月贷后检查时才发现抵押活牛缺少200头,2024年1月监管头数仅剩余110头。从贷款发放到发现问题,相隔近一年时间,这期间银行对抵押物的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按照监管要求,对于活体动物这类易损耗、流动性强的抵押物,银行应当建立更加频密的核查机制,但吉林银行显然没有做到。更为严重的是,案件中还暴露出银行内部人员收受“好处费”为审批开绿灯的情况。这种内外勾结的模式意味着银行的风控体系不仅存在技术性漏洞,更存在道德风险和制度性腐败。当利益输送成为潜规则,再严密的风控制度也将形同虚设。
2024年10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松原监管分局披露,吉林银行松原分行因“通过以贷收贷、以贷收息的方式,掩盖了贷款的实际风险状况”被罚款30万元。这种掩盖风险的操作手法与本案中刘某能够在已有逾期贷款的情况下继续获得新贷款的情况高度吻合,说明该行在风险识别和风险分类方面存在系统性问题。当银行为了账面数据好看而采取不合规手段掩盖风险时,实际上是在为更大的风险爆发埋下伏笔。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吉林银行包含个人和分支机构共收到31张罚单,累计罚款540万元。从处罚原因看,贷前调查失实、贷后管理失职、资产风险分类不准确等问题反复出现,说明该行的内控缺陷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梳理吉林银行近年来的违规记录,2022年12月,吉林银行在一周内连收12张罚单,累计罚款440万元。违规事项中,“贷款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和“资产风险分类不准确”均两次出现。这种“屡查屡犯、屡罚屡犯”的现象反映出该行在整改方面流于形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25年6月,吉林银行长春分行因“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被罚款50万元,时任长春新区支行副行长被罚款5万元。反洗钱是银行合规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金融犯罪的重要防线。该行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失职不仅可能导致银行被不法分子利用,也说明其内部管理的松懈程度。从罚单涉及的人员看,2024年已有10位分支行行长被警告,这意味着平均每月就有一位行长领取罚单。如此高频率的管理层问责一方面说明监管部门加大了处罚力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该行在选人用人、绩效考核、问责机制等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当分支机构负责人频繁因违规被处罚,总行层面的管理和监督责任同样值得追问。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吉林银行的内控缺陷不仅体现在业务层面,还渗透到了公司治理结构中。2019年至2022年间,该行多位高管相继落马。2019年11月,原董事长张宝祥被查,2026年12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26年12月,原副行长杨盛忠被双开,2026年2月以贪污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18年12月,原副行长王安华被查,2026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高层管理人员相继落马的背景下,该行的内控文化和合规意识可想而知。
除了管理层腐败,员工层面的违法犯罪也时有发生。2019年4月至2026年10月间,吉林银行延吉分行员工朱世杰利用银行员工身份,虚构“倒贷”投资业务,承诺返高利息,骗取被害人733.7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赌博,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1个月。2026年,辽源分行的一名员工通过相同手法诈骗了142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这类案件的频繁发生,说明该行在员工管理、职业道德教育、异常行为监测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吉林银行近期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这家区域性城商行在资产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正面临资产质量承压、盈利增速放缓与资本约束加剧的三重挑战。截至2025年6月末,该行总资产突破8170亿元,较年初增长9.55%,存款规模亦稳步提升至5990亿元,显示其区域金融主力军地位稳固。然而,规模扩张的背后,核心财务指标的波动折射出深层经营隐忧。2025年上半年,吉林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至1.57%,较年初增加0.07个百分点,延续了2023年以来连续三年上升的态势。关注类贷款余额虽较2023年峰值有所下降,但295.77亿元的存量规模仍占贷款总额的6.25%,潜在风险敞口高企。联合资信评级报告指出,该行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及制造业贷款占比超六成,其中房地产业贷款占比5.52%,住房按揭贷款占比14.47%,在行业下行周期中面临较大信用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2024年该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例达8%,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比高达55.42%,客户集中度风险突出。
尽管202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48%至88.44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增速已从2023年的18.35%大幅放缓至5.31%。信用减值损失的持续高企成为主要拖累因素——2024年该行计提信用减值损失53.27亿元,较上年增加10.27亿元,直接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25.09%。这种“增收不增利”的矛盾在2025年一季度更为凸显: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2%至40.7亿元,仅靠拨备覆盖率下降(从2023年的168.17%降至2024年的163.31%)释放利润空间,才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4.2%的短期反弹。
作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城商行,吉林银行与股东的关联交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该行向关联方发放贷款余额达128.99亿元,其中对亚泰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贷款超82亿元。而亚泰集团自2026年以来累计亏损超115亿元,2025年一季度仍亏损4.7亿元,其拟转让3亿股吉林银行股份的举动,暴露出股东流动性危机可能向银行传导的风险。
)
)
)
)
)
)

)
![[VirtualLab论文] VirtualLab Fusion仿真精密玻璃模压成型所造成的衍射条纹(virtuallab软件)](/img/76.jpg?text=[VirtualLab论文] VirtualLab Fusion仿真精密玻璃模压成型所造成的衍射条纹(virtuallab软件))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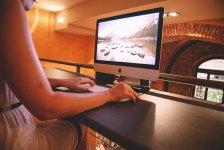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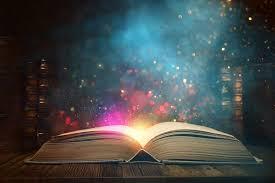)